零壹Lab | 何谓“数位人文学”?
发布时间: 2018-04-27 林富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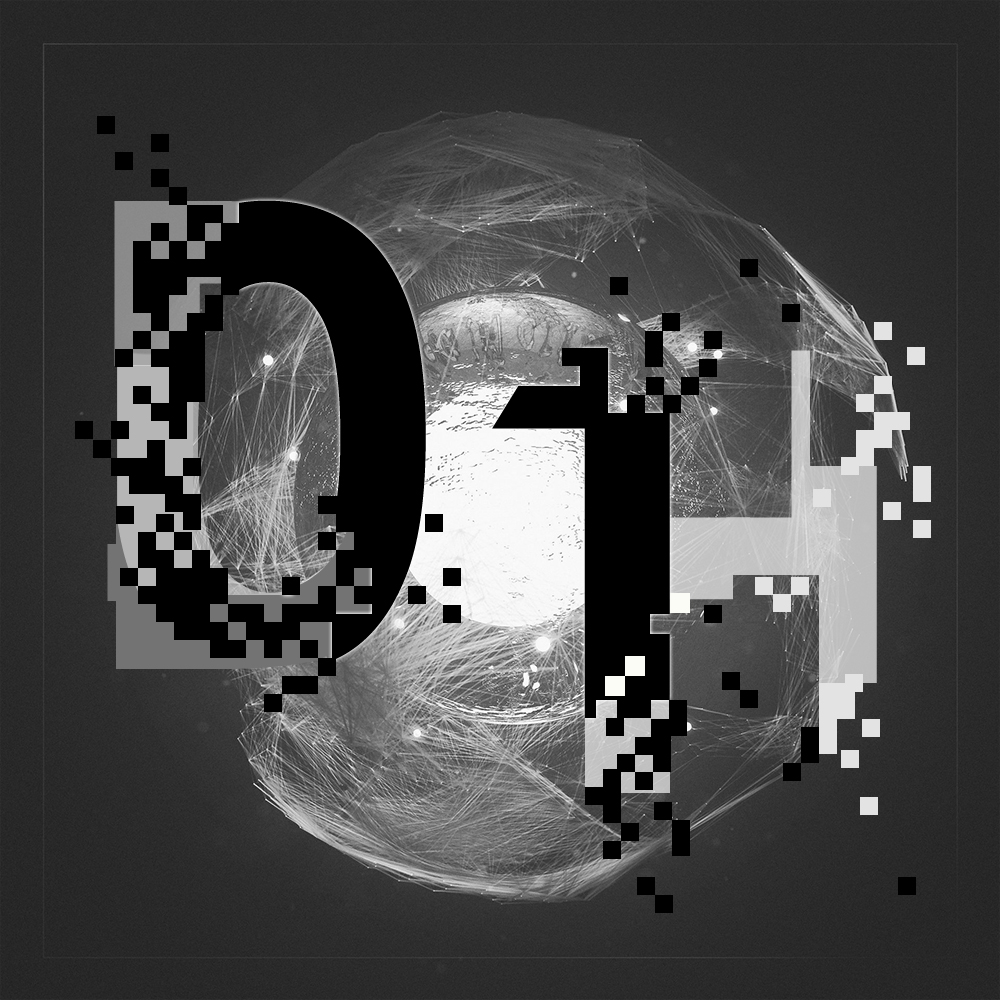 公众号:lingyilab
公众号:lingyilab
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人物简介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数位人文学”研究室召集人、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召集人。1980年代即投入台湾数位文化建设工程行列,曾任《数位人文推动计划:「数位人文学」白皮书研订计划》主持人(2014-2017年)。

引言
1984年,中央研究院开始推动“史籍自动化计划”,在1980至1990年代,不仅创置了独步全球的汉籍全文资料库,也奠定了台湾人文学与资讯科学携手合作的基石,并吹响了“数位革命”的号角。其后的“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2002-2007)与“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2008-2012)则是进入攻城掠地、宣扬理念的阶段。而就在“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结束之后,国科会人文处(现为科技部人文司)随即在2013年开始推动“数位人文主题研究计划”,算是成功的接续了这场革命的火种。
然而,究竟什么是“数位人文学”?应不应该发展“数位人文学”?各方人士的看法仍然相当分歧。因此,我们有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检视这个领域的发展历程、具体内涵、涉及的知识范围与社会层面,并且反思台湾在这股浪潮中应有的作为。
数位革命的效应:人文的观点
“数位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以下简称DH)其实是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名词,算是数位时代的新生儿,但是,成长的速度却相当惊人。十余年来,以此为名或与此相关的论文、专书、课程、科系、机构与组织纷纷出笼,数量不断增长,地域持续扩散。影响所及,已从大学校院蔓延到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界与传播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
不过,要认识DH,必须先了解数位科技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1. 微缩效应
人类文明的第一次突破,在于能利用大脑的记忆能力储存经验,并利用“语言”传播经验。到了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又创造了书写工具和表意文字,经验因而可以脱离身体的限制,能较长期而准确的保存下来。其后,一千多年前发明的印刷术,更让知识与资讯的复制更为快速,扩散的幅度更加广泛。至于十九世纪所发明的录音、照相、录影技术,则是让声音、图像、影像也能快速的储存与传播,尤其是收音机、广播电台、电视与电视台等传播媒体在二十世纪出现之后,资讯与知识的传送速率与幅度更是大幅提升。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数位科技则进一步带来了惊人的“微缩”革命。原本以各种实体储存的文化内涵,必须耗用大量的媒材,占用庞大的典藏空间,但是,透过数位化处理,便可大幅缩减其体积和重量。而含藏同样资讯量的“原生数位”资料,所占据的储存空间更小。因此,这可以说是“物体/媒体微缩”进而促成“空间微缩”。
此外,数位科技准确、快速、廉价的复制及传播能力,无论在速度、数量、距离方面,都不是口语、文字或实体媒材所能比拟。因此,数位化所引发的“微缩”效应,还包括提升大家近用(access)文化资产的机会和效率,让使用者与资料之间的“距离微缩”,让取用资料的“时间微缩” 。而且,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专家与民众之间、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数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也可大幅缩小,让“落差”“微缩”。
2. 大数据(巨量资料)(BIG DATA)
在数位时代,人类生产、复制、改造、传播与再生产知识与资讯的能力、效率与速度有了重大的突破,网路世界因而随时随地充斥、流通、增长着巨量的资料,这也就是俗称的“大数据”(Big Data)。
“大数据”基本上是指无法以人工的方式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收集、整理的资料,而且,资料量通常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必须借助特殊的数位科技的方法和工具才能分析。
“大数据”带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大冲击和改变,不是资料数量的增加,而是分析、处理资料的方法,观察和描述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角度,以及呈现探索结果的工具和形式。
3. 数位汇流(DIGITAL CONVERGENCE)
“大数据”的出现和“数位汇流”息息相关。所谓“数位汇流”意指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将原本以不同形式或不同媒材所呈现的资讯,汇聚成可以在同一载具或平台显示的数位资料。而原本独立发展的产业及媒体,如电子、资讯、通讯、电影、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等,也因此可以汇合成一种新的整合型的产业或“新媒体”。
这意味着人文学者所要处理及产制的往往是一种多媒体的数位文本,而取得资料、传播知识的通路将更加仰赖数位媒体。
4. 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
由形形色色的个人装置和网路设备连结而成的网路世界,可以说是人类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所建构的一个“虚拟世界”。
这个虚拟世界无法脱离真实世界而独立存在,有些内涵和运作模式也只是现实世界的翻版或补充。人类进入网路世界之后,一样可以进行各种惯有的日常活动,而且,经常与真实世界的活动相互连系、延伸与互补。然而,两者之间有时也存在着竞争或替代关系。
因此,凡是想要探究当代及未来世界的人文学者,必须出入实体与网路世界,才能完整的观察、分析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行为,及其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
5. 多语情境
电脑网路穿透、打破了原本被政治、宗教、语言、种族、性别、年龄、阶层、职业等因素所区划的人群界限,建立了较为通畅的往来管道。但是,即使在网路世界,各种自然语言所形成的壁垒与障碍依然存在。
更棘手的是,网路世界的多语情境还添加了“人工语言”。无论是作业系统还是应用程式,基本上都是由某种特定的程式语言撰写而成,而这种人工的“符码系统”,不仅用来沟通人与机器,也让不同的机器可以串接或交换资讯。然而资讯界要达到“书同文”的境地还相当困难。
此外,各地的网路族在彼此频密往来、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了新的词汇和一些新的“符号”及“代码”语言,让“外人”难以理解。
未来,人文学者若要在网路世界中生活并从事研究工作,势必要掌握多样的语言。
6. 移动、连结与全球
当然,“人工智慧”的发展,会让自然语言的语音辨识、转译和语文翻译,乃至图像解译的速度和准确度逐步提升。有朝一日,自然语言所造成的沟通障碍将可大幅降低,让人类在网路世界的移动更加自由而快速。若再加上云端科技以及行动装置的普遍运用,那么,“全球一家”的理想便会在网路世界中实现。
全球格局一旦形成,人文学者惯常的区域(国家)与“在地”研究方法与视角,势必要改弦易辙。
“数位人文学”的诞生
在上述情势之中,人文学者开始拥抱数位科技是自然之事,“数位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因而诞生。
1. 语词与概念
但是,DH这个词汇究竟是谁所创或首度使用,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知道苏珊‧史莱布曼Susan Schreibman)等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数位人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Oxford: Blackwell, 2004)已经使用这个词汇和概念。不过,词汇的出现和DH的诞生不能等同视之。
假如我们将DH简单的定义为“运用数位科技进行人文研究”,那么,其开端至少可追溯到1949至1970年代兴起的“人文计算学”(Humanities Computing),或是1980至1990年代以建立“电子文本”(E-Text)和“数位典藏”(Digital Archives)为核心工作的人文学研究。
不过,2004年依然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有一群来自资讯科学、图书资讯学及各个人文领域的专家共同发声,亮出DH的旗帜,不仅回顾其前身(人文计算学)的发展历史,也尝试将DH界定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说明其方法、工具及在各个传统人文领域的可能应用。从此之后,DH逐渐成为数位科技与人文学交界地带的主流代称,但是,至今依然是一个变动、演化中的概念。
2. 组织与机构
在DH的推动者提出说帖之后,很快的就获得了回应。最明显的就是一些以DH为名的组织和机构陆续出现。例如,全球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DH组织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ADHO)在2005年年底便正式宣告成立。更重要的是,从2006年起,欧美各国(美、加、英、欧盟等)纷纷以国家资源补助以DH为名目的研究计划,而不少教育、研究机构也开始设立以DH为名的单位。这种机构性的建置,让DH在大学体系中找到了位置,获得了资源和照护,并开始生根、成长。
3. 课程与学位
要发展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最终或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必须能开设课程以传达、创新及积累知识,而且终究必须授予学位,才能培育该领域或学科的人才。然而,真正以DH命名的系所还相当少,似乎只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于2011年开设的数位人文学系(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而且从大学部到硕士班、博士班都有。但是,辅修(学士班为主)或授予学位(硕、博士班为主)的DH学程的大学却不少,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德国、法国、日本、澳洲、纽西兰等国都有。
4. 认同与传播
透过实际的研究、教学、会议及专案计划,DH的倡议者和跟随者逐渐形成交流密切的学术社群,再加上DH的成员惯于在网路世界活动,因此,其社群的经营以及资讯和知识传播,几乎都会运用各种最先进的数位媒体,扩散的幅度、速度都相当惊人。而在虚实并进、亲密互动的过程中,“认同”DH的学者逐渐增多,DH scholar或digital scholar这个词汇开始被用来和传统的人文学者作区隔。
“数位人文学”的内涵
在DH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不少人都抱持肯定的态度,并尝试给予清楚的定义和定位,但是,极力拥护、追随者有之,负面的批评却也不少。无论如何,这已经算是一个新兴领域或学科,至于其具体内涵,我们只能利用既存的著作、课程、案例,大致划定其范围,介绍其所使用的材料、技能、方法,并以传统人文学的范式做为对比,说明其特点。
1. 范畴
基本上,DH是指结合了数位科技与人文研究的一门学问或学术领域,主要旨趣是利用数位科技探讨或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或是从人文的角度探索、反思数位科技如何形塑人文世界。我们虽然难以划定其边界,但是,凡是“不使用或不涉及数位科技的人文研究”,或是“所要探讨的对象或要解决的问题不属于人文研究的领域”,都可以比较清楚的排除在外。
2. 材料
DH和传统人文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其所运用的材料都是“数位资源”(digital resources),包括了“数位化材料”(digitized material)和“原生数位材料”(born-digital material) 。前者是指将原本以非数位方式储存或呈现的资讯、资料、物件,转化为数位格式。 “原生数位材料”则是指直接利用数位工具(如数位相机、数位扫描器、数位录音机、电脑等)生产的数位资料,而且没有相对应的非数位(实体)资料。
3. 工具与技能
无论是要生产、管理,还是要展示、传播知识,DH的学者必须利用一些数位工具与技能,而其常用者大致可以分成下列四大类。
- 第一是基本工具,也就是电脑、摄影机和所谓的“办公室套件”,包括:文书处理、简报、试算表、资料库管理、通讯等软体,以及用以处理图表、图像和影像的工具、和设计网站的工具。
- 第二是资料的搜集与管理工具,包括各种搜索引擎和资讯检索工具,以及资料库管理系统。
- 第三是资料的分析与探讨工具,包括各种“资料探勘”或“文本探勘”、文本或图像(影像)辨识或“比对”工具。
- 第四是资料的呈现与传播工具,包括各种“资料视觉化”(Data Visualization)工具、“数位出版”工具、展示与传播网站(平台)。
4. 方法与途径
由于DH所面对、处理的通常是巨量资料,且必须使用数位工具,因此,在研究、探索问题时往往会采取一些和传统人文学有所差异的方法。
首先,在阅读方面,由于大半是采取“机读”(机器阅读)的方式,因此,逐字逐句的“细读”(Close Reading)、诠释字里行间的意义,便难以进行。反之,以“鸟瞰”(Distant Reading)式的观察或“宏观分析”(Macroanalysis)的方法,探讨人、事、物在时、空中的分布,勾勒主要发展趋势和重大变迁阶段,或是寻绎文本、社会的结构与关系,便成为DH常见的阅读方式。
其次,人物向来是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传统的人文学者通常会偏重于探讨个别人物或特定人群的行为、心理和活动,但DH的学者则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和工具,剖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并探讨资讯、知识、资源、权力如何在人际网络中产出与流转,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有效的探讨由网际网路所建构的“虚拟社群”。
再者,地理资讯系统(GIS)的导入,不仅是为了资料呈现的视觉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人文思维的空间向度。 GIS格外适用于探讨人文研究的移动(旅行、交通、移民、传播等)、聚落(城市、乡村等)、建筑、物产、人口(族群、语言)等问题,也可以用来检视“网路世界”的资讯流向和空间分布。
此外,过去的人文学者,从搜集、整理、分析资料,到撰写、发表研究成果,大多数都采取单打独斗的“独立”(或孤立)研究。 DH的学者则不然,众人“协作”逐渐成为常态,尤其是人文学者与资讯科学家或资讯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更是不可或缺。所谓的“群众协作”(Crowdsourcing)则可以用来协助研究者搜集、整理,甚至是分析资料。至于各种协作平台等则常被用来进行群体的协同写作。有些数位博物馆甚至会开放其藏品及网页空间供阅听者自由进行线上策展,并上传、补充策展人自己的藏品,这也让知识的建构和传播更具“民主”色彩和群众性格。
结语:湿婆(Siva)来了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DH在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生根、发芽,但尚未茁壮、长大。其他各国则或多或少已经耳闻、接触或开始耕耘DH这个领域,台湾也不曾落后。而无论DH的未来会如何,数位科技正主导人类文明的走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以人类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还是必须对此有所掌握、思考与回应。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资讯科技所创造的“数位世界”,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将人类文明推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就像印度的湿婆(Śiva)神一样,数位科技既是创造之神,也是毁灭之神。当“物联网”(LOT)逐步建构成形之后,人也会成为身陷网络之中的“万物”之一。未来,透过身上或体内的“装置”,我们随时都会将个人的位置、生理、情绪、行动、行为,以及接触之“物”,向网路世界传送,并被他人所掌握与利用。个人“隐私”恐将退缩到小小一隅,或完全消失。
其次,当“智慧城市”(Smart City)建构完成之后,我们在公共空间的一举一动,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政府及企业的监视、记录与控制之中,任何“逾矩”的行为与行动,都难逃检举、控诉与惩罚,甚至连企图“违规”都不可能。城市将成区域广阔的监狱,人类则形同囚徒。
更惊人的是,随着各种“虚拟实境”(VR; AR; MR)技术的精进与运用,未来人类在“网路世界”的感官经验与心灵活动将更趋近于在实体世界的经验,有时甚至更加敏锐、强烈且可以任意操控。当“虚拟实境”结合了“物联网”和“智慧城市”之后,人类在网路世界的移动与体验便会类似科幻电影所描述的“时空穿越”,或是出入道教所说的“洞天福地」”(神仙世界),或是一如北亚“萨满”(shaman)的“魂游”(ecstasy)、台湾童乩、“尪姨”的“观落阴”。而随着进入、停留在网路世界的时间不断增加,人类在虚拟世界的心灵活动时间便会超越在实体世界的身体活动,届时,身心解离的现象便会频频出现。这究竟会引发何种社会效应或物种变化,难以预测。
总之,数位世界已经成形,未来将如何演化,人类要何去何从,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无力掌控变局,但是,透过DH的开拓与探索,我们至少能观测、记录、反思这样的发展,并适度的提供一些警示与对策。当然,DH究竟会带来“创造性的破坏”还是“破坏性的创造”,究竟是开辟天堂之路还是开启地狱之门,也有待验证。然而,无论接不接受、喜不喜欢DH,人文学者还是无法逃脱数位科技所带来冲击,旧的生活方式、认知行为、思考模式、学术“典范”,在二十一世纪也将会有重大的变革,毕竟“数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人数将逐渐超越“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附记:本文系根据《“数位人文学”概论》改写而成,原文详见林富士主编,《“数位人文学”白皮书》(台北: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2017),页1-36。
此书信息见:http://ascdc.sinica.edu.tw/single_news_page.jsp?newsId=2525
可以访问以下网站注册会员,浏览电子书全文:
http://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3971
https://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33905
http://www.airitibooks.com/Detail/Detail?Public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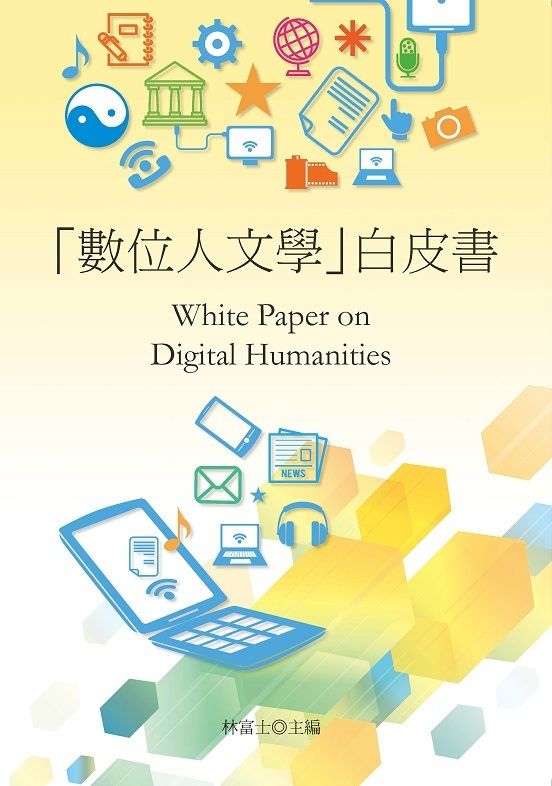
出版资讯:林富士,《何谓“数位人文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19:2(2018.3),页93-100。
https://www.most.gov.tw/hum/ch/list?menu_id=cefde66d-4f4f-4116-aba7-04a42f48d9df&filter_uid=39ac37b0-8b29-4715-aa0a-f40cca095c3f&listKeyword=&sortBy=&pageNum=1&pageSize=18&view_mode=listView&tagUid
【转载得到林富士老师授权,谨此致谢!】
责编:徐力恒 顾佳蕙 美编:傅春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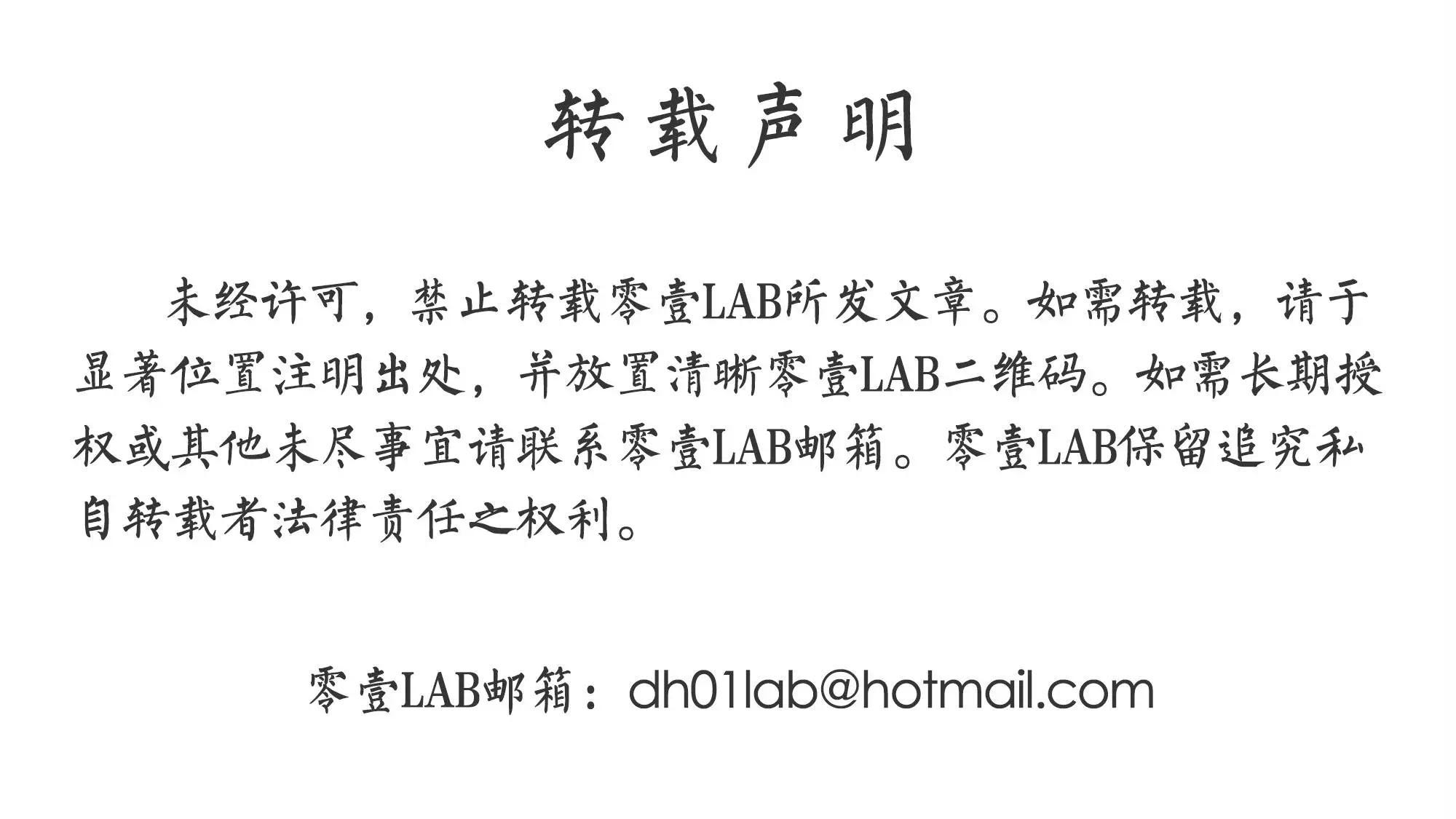

关注零壹Lab,获取更多数字人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