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Lab | Breaking through the crisis: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ate: 2017-05-15 [Original]Jing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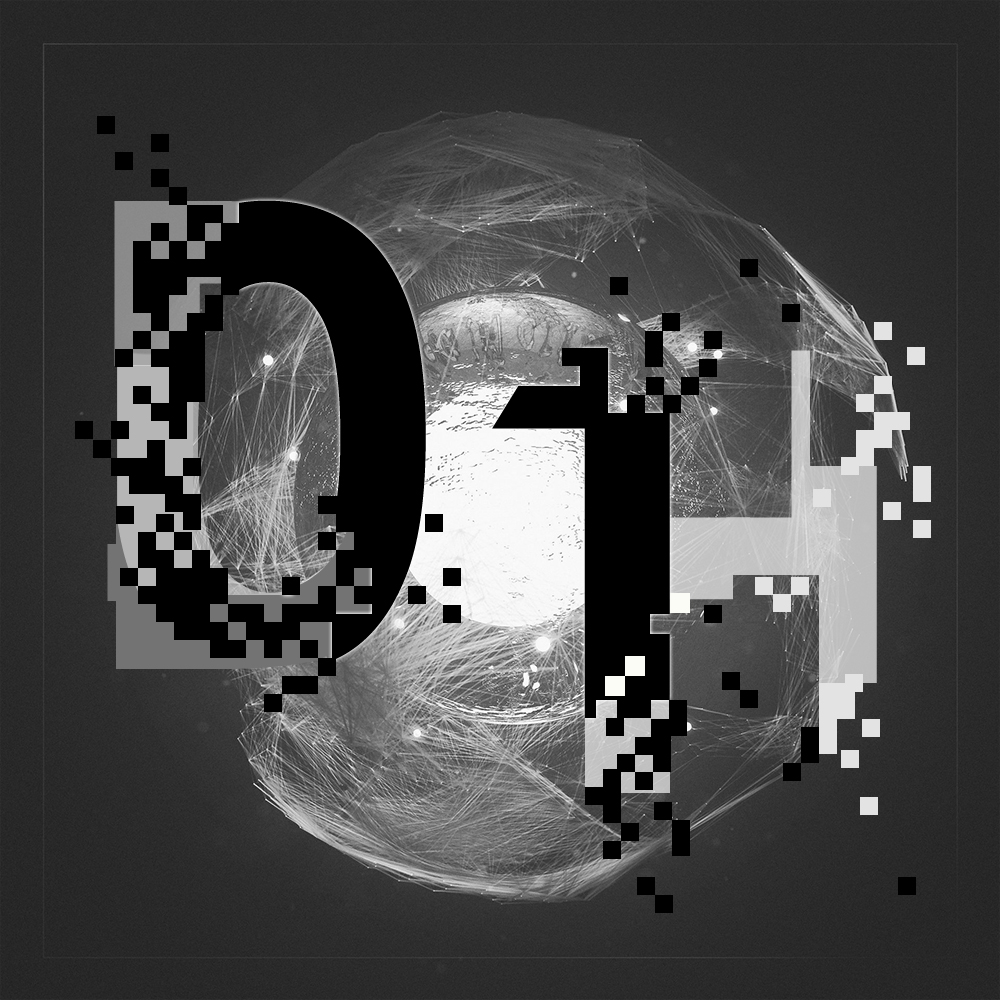 公众号:lingyilab
公众号:lingyilab
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数字人文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是整个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结合英美学界的情况去看待数字人文的出现去看:一方面是传统人文学科开始将数字文化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思想问题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这个范围就非常广阔,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 数字人文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人文学科发展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则是 数字人文是对那些将数字技术施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的统称,这种施用所导致的结果包括了方法论上的革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的研究问题的出现 。这两方面的合力使得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复杂和多样,而采用“数字人文”这个名称来统称繁多复杂的各种现象本身就带来了一些问题。 比如数字人文是否真正挑战了传统的人文学科?数字人文对传统人文研究的突破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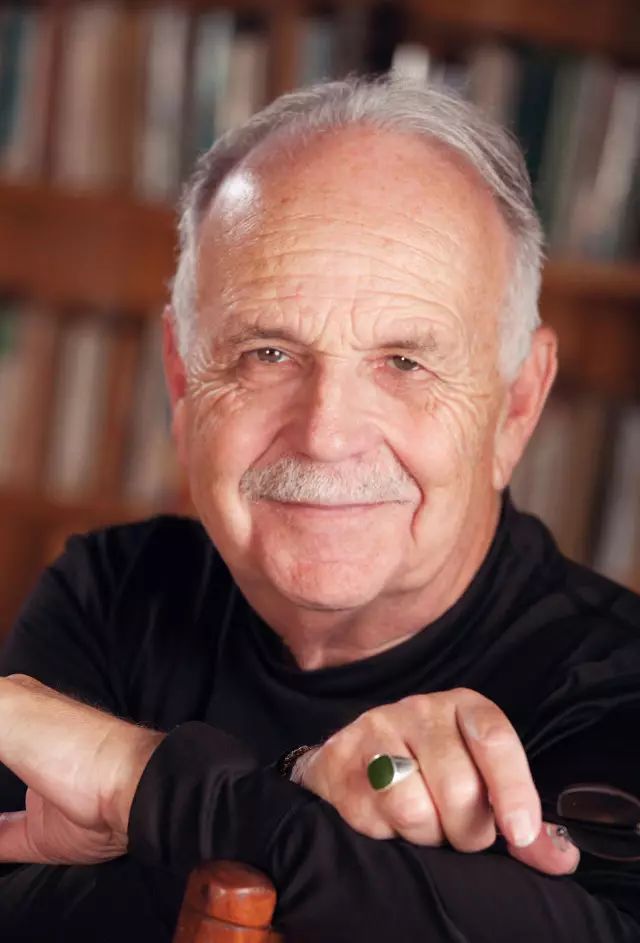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斯坦利·费什教授就在他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了传统人文学者的这种关切[1]。在这篇名为《数字人文及其不朽》的短文中,费什教授非常经验性地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提出了数字时代传统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挑战:“……还因为博客总是暂定的、瞬息的、交互的、公共的,随时被质疑的、中断的、可窜改的,以及无意终止的。而我在至今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致力于建构一些具有决定性、丰富性、不朽性和确定性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论述都是我自己的。”[2]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人文研究且德高望重的学者,费什教授写文章来分析数字人文对学科的影响,表明了他对数字人文的态度:是值得被研究的对象;更有趣的是,他还从自我经验出发,清晰地意识到数字人文所宣称的一切正是和他在过去50年所努力奋斗追求的成就相冲突的。无论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真实的情感表达,这篇文章开头的两段都清晰地表明了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了人文学者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或者说数字人文已经让传统人文学者开始严肃对待起来,数字人文不是小事,而正如马修·戈尔德(Matthew K. Gold)在《数字人文的时刻》(The Digital Humanities Moment)中说到的,“最近在流行出版物,比如《纽约时报》、《自然》、《波士顿全球》和《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的有关数字人文的诸多报道都已经证实了数字人文不像《纪事报》在2009年报道的那样,仅仅是‘下一个大事件’,而就是一个‘事件’,正如同一个报纸在2011年报道的那样。”[3]但是对于像费什这样的资深教授而言,数字人文这样的新事物是大事件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其“伟大”之处更多的是通过这个群体自己的摇旗呐喊所证明的。因此费什教授对数字人文所宣扬的主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对传统观念中的“作者”和“文本”的批判是数字人文的切入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菲茨帕特里克教授所提出的“过程中的文本”概念消解了单一、权威作者和稳定、指向文本的存在意义;而当作品成为意义的链条,权威作者成为文本参与者的时候,意义的生产就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依托的东西。费什教授颇有些讽刺意味地将之比拟为弥尔顿《失乐园》中没有终结、只有过程的“神秘舞蹈”,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这里并不明确谁是“主体”)从时间、意义甚至是宿命中解脱出来,沉浸在“神性”(在这里等同于“数字性”)的迷狂中。在他看来,这种太过“轻易”地与宿命的抗争恰恰是一种数字人文所反对的线性思维,因为数字人文总是许诺在数字时代到来以后,一切因旧的权威所引起的病症都将会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被治愈。而与此同时,费什指出这样的许诺并非那么单纯,事实上其背后至少有两个政治性因素,一个是对于过去几十年来高校专业化、学科间沟壑日益加深的革命性反抗;另一个则是年轻学者们试图通过这种技术上的“先天优势”来反抗在科研经费日渐微缩情况下的悲惨处境。同时,费什教授根据数字人文研究者的说法,总结了数字人文可能具有的“优点”:打破大学的墙壁让更多的人进入“校园”和教给学生一些“职业”技能。最后,他似乎“不经意地”却又“意犹未尽地”抛出了一个问题:“数字人文真的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文目标(和人文工作)的理解吗?”他接着用数字人文的先驱性人物,杰罗姆·麦克盖恩(Jerome McGann)的观点进行了回答。当然,答案的概要是,请听下回分解。

应该说,费什教授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数字人文的出现确实有着当代学术大环境的影响,美国教育财政预算逐年减少,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科研经费也不断被削减,尤其是2007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危机使得很多大学出现薪酬停涨和岗位减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文学科博士们毕业,进入求职市场找工作,他们面对的生存与竞争压力可想而知。同时,就算是那些已经在高校获得教职的年轻学者们,也面临着相似的生存难题:很多原本是终身教职的全职工作被削减为兼职的临时工作;岗位工资被减少,连年不涨薪;项目经费紧缩,研究难以获得资助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领域无疑为人文学科的年轻学者们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通道:新学科的建立往往意味着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科研岗位的增加和研究经费的支持。这一方面可以从近20年来各种数字人文研究机构的建设看出来——每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都需要数字人文方面的专家,而这主要都是中青年学者;另一方面,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EH)的“数字人文办公室”每年都要提供几十万美金的科研经费来支持美国的研究机构开展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项目。与此同时,NEH还与美国本土的自然基金会(NSF)、英国的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加拿大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会(SSHRC)联合举办了“the Digging Into Data”的竞赛,鼓励这几个国家间的团队合作,共同开展相关的数字人文研究课题,2011年几个机构就此竞赛提供的科研资助总计达到了640万美金。这足以让年轻的学者们感到欢欣鼓舞了。

此外,年轻学者们为此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数字出生(digital born)的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逐步熟悉了数字媒介环境及各种硬件和软件的应用。他们很自然地就将数字媒介应用于他们的研究之中,这不需要他们去做知识结构的调整或者补充。相反地,他们在这种自由的结构转换中发现了自身的优势,他们比上一代的年长学者们更加容易地去适应新的技术需求,更敏感的发现新的学术问题、更加方便的与学生开展交流。同时,也更加灵活地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在这点上,他们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让他们尝到了技术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的甜头,他们自然反过来更愿意推动这个新的学科、新的研究导向、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教学法的发展。费什教授将之成为是政治性的,确实不为过。但他也忽略了一点,数字人文的发展是有其历史脉络的。之所以现在出现大量有关数字人文的论文和著作的原因也是因为在过去40多年的积累中,形成了大量的数字技术、数字项目的成果和实践经验,这种历史的发展使得年轻的学者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去为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摇旗呐喊,为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一切进行辩护,为他们可预见未来进行欢呼。
注释
[1] Stanley Fish,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 2012-01-09, 9:00 pm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1/09/the-digital-humanities-and-the-transcending-of-mortality/
[2] Stanley Fish,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 2012-01-09, 9:00 pm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1/09/the-digital-humanities-and-the-transcending-of-mortality/
[3] Matthew K. Gol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oment”,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tthew K. Gold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
主编:陈静 责编:徐力恒 顾佳蕙 美编:张家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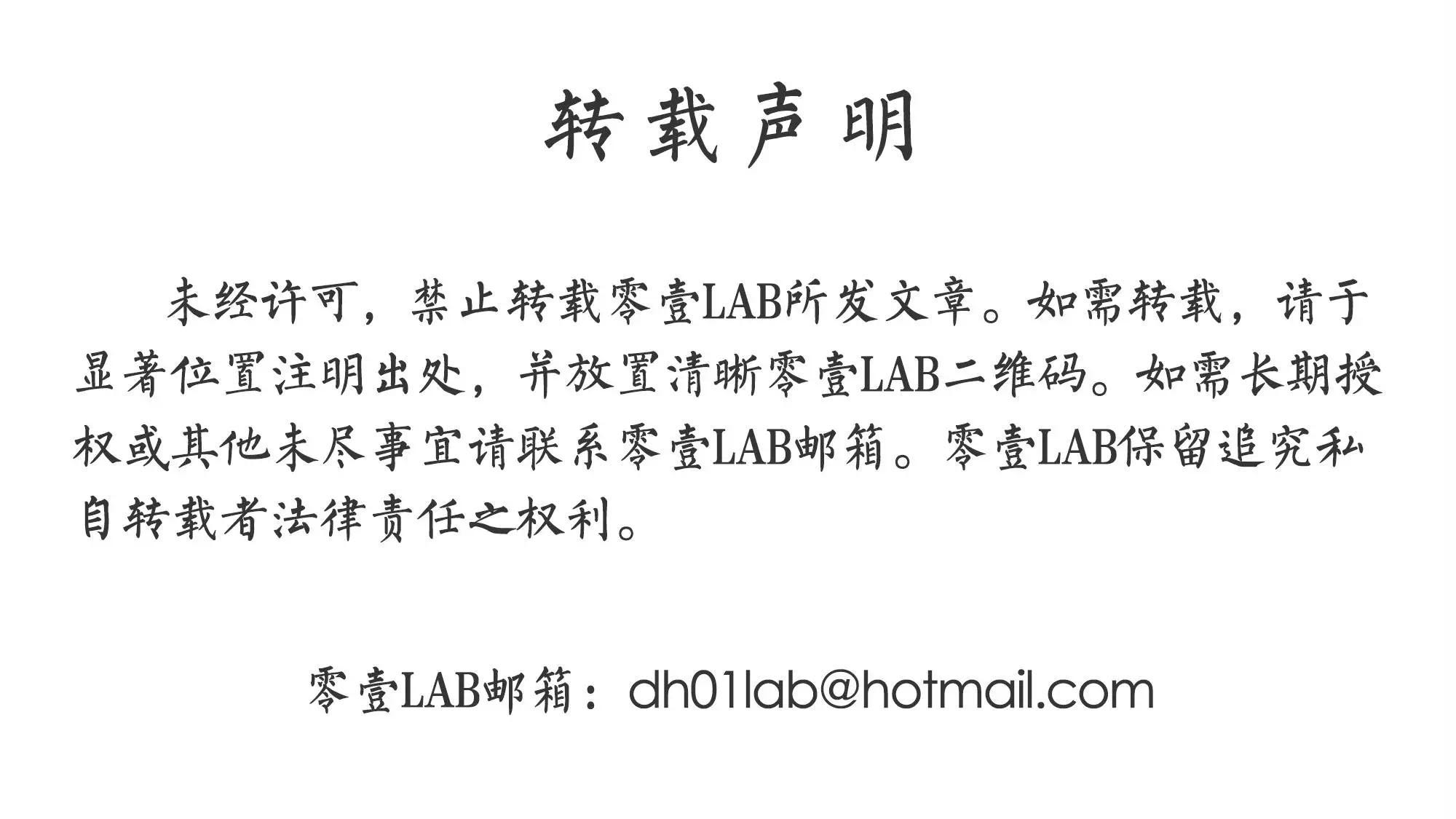

关注零壹Lab,获取更多数字人文信息!